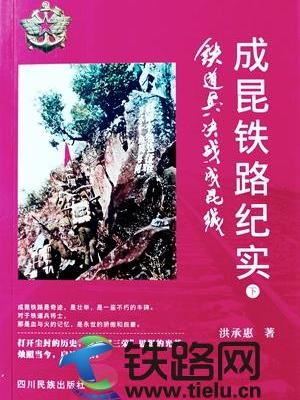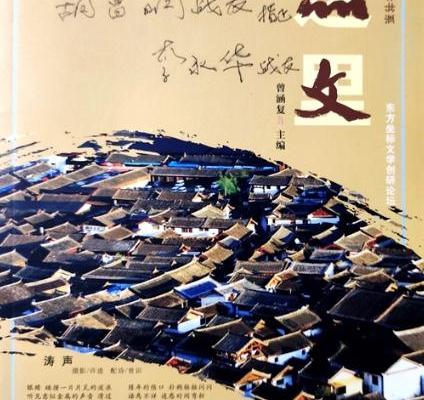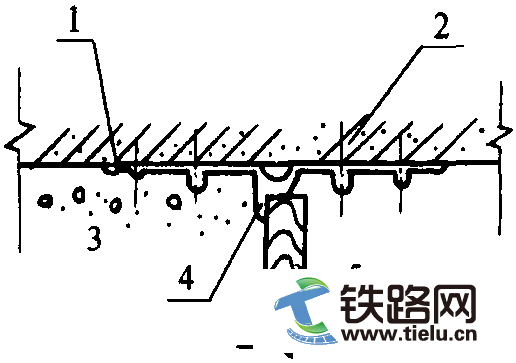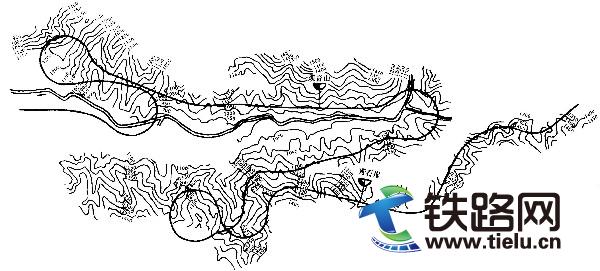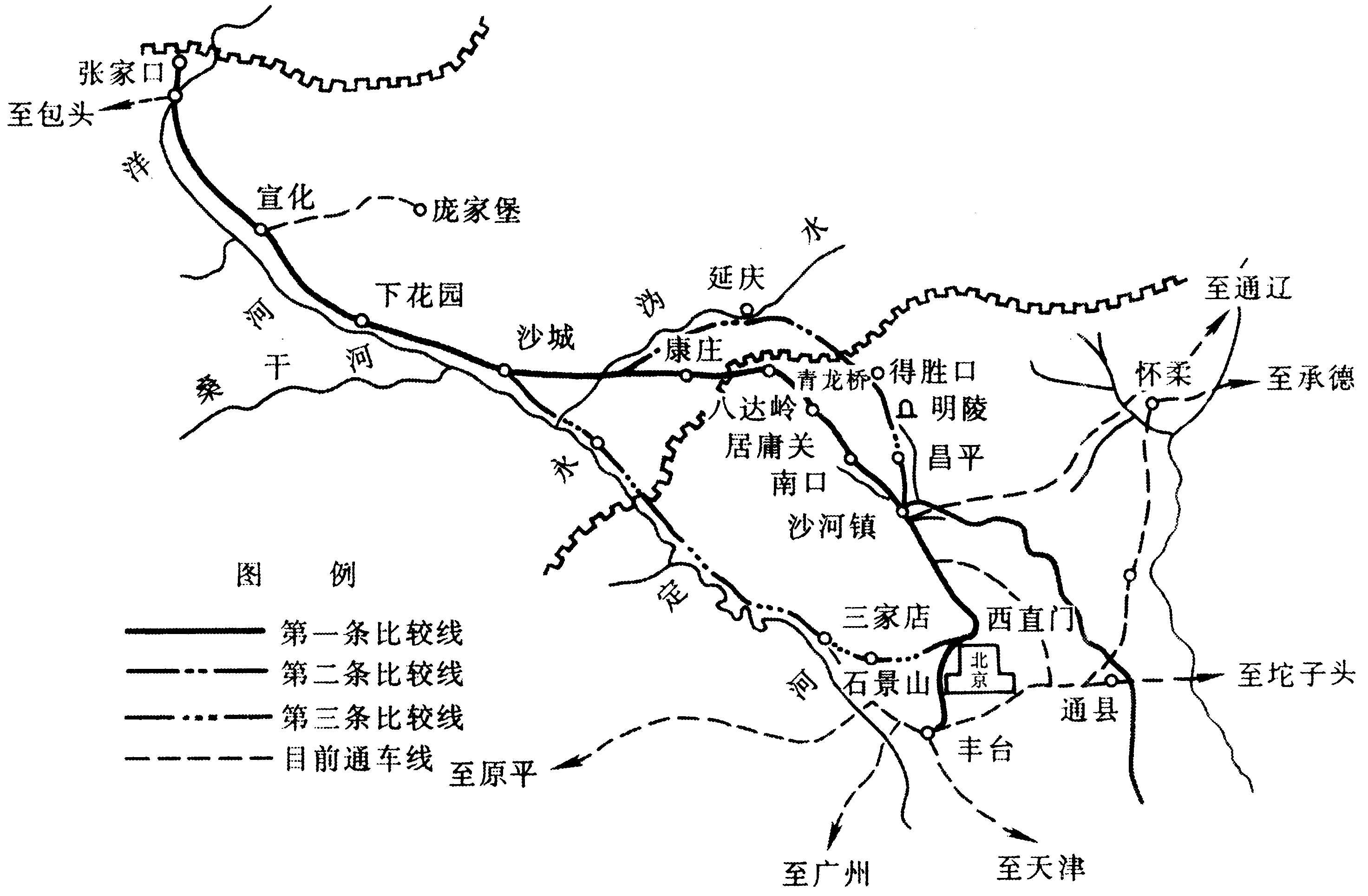五樓宣傳科那扇朝西的窗臺上,永遠倔強地立著半截白粉筆。那是老王的“老伙計”,打從他四十年前從苗嶺深處的鐵路小站調進機關,這粉筆就沒離開過他。每當構思那些關乎鐵道線上奮斗與榮光的材料時,老王總愛在蒙著薄塵的玻璃上劃拉提綱。那些霜花般的字跡,在落日熔金的余暉里,仿佛被賦予了生命,化作液態的金箔,順著暖氣片在玻璃上洇出的細微溝壑緩緩流淌,映得整個辦公室都暖洋洋的,充滿了人文的溫度。直到一年前,那臺锃亮的AI寫作終端像個沉默的鋼鐵巨人進駐辦公室,顯示屏幽幽的藍光便如漲潮的海水,帶著不容置疑的科技力量,一寸寸吞沒了粉筆末在陽光下細碎而溫暖的閃光。
機器吐出第一篇關于“春運新風貌”的講話稿,只用了令人咋舌的十秒鐘。老王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酸澀的眼睛,又重新戴上,盯著屏幕上那排整齊劃一、毫無瑕疵的仿宋字體,感覺像在看一份精密的零件說明書。他的手指懸在膝蓋上方幾厘米處,無意識地劃著一個又一個看不見的頓號和逗號,那是他握了半輩子粉筆和鋼筆養成的習慣,如今卻像被抽走了秤砣的老秤桿,在虛空中徒勞地尋找著熟悉的平衡與節奏。那些他曾字斟句酌、精心“調味”的排比句——比如把工務職工在崇山峻嶺間扎根堅守的精神比作“青松咬定懸崖不放松”,把風雪中堅守崗位的身影喻為“鋼軌上的燈塔”——此刻在屏幕上,都變成了標準化生產線上的螺釘螺母,精準,卻冰冷,連比喻都帶著流水線特有的、刺鼻的機油味,失去了往日的溫度與靈氣。
最初的日子,老王有些失落,甚至感到一絲被時代拋棄的恐慌。他開始在每個萬籟俱寂的深夜,悄悄給那臺冰冷的AI投喂自己的“私藏”。泛黃發脆的《苗嶺彩虹》雜志剪報——那是他年輕時采寫的通訊,記錄了小站職工如何在塌方的險境中搶修線路——被小心翼翼地塞進掃描儀,老花鏡片上因呼吸而浮起的細小塵埃,在臺燈的光柱下,如同無數微型銀河在鏡面緩緩坍縮、旋轉。當他曾經飽含激情寫下的“抓鐵有痕、踏石留穎被AI自動轉譯為“數字化改革攻堅,實現效能躍升”,當“老黃牛精神”被冷靜地解讀為“提升算力集群效能,優化資源配置”時,老王忽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憋悶,猛地推開了窗戶。秋夜微涼的風裹挾著遠處鐵道線上隱約的汽笛聲涌進來,卷走了窗欞間他方才用粉筆寫下的二十三個歪歪扭扭的字——那是他心中尚未被算法格式化的、屬于人的吶喊,像一群撲向路燈的飛蛾,在AI終端幽幽的藍光里,悲壯地撞出幾點轉瞬即逝的細小火花,旋即湮滅無蹤。
苗嶺侗鄉的秋雨來得纏綿悱惻,空氣里彌漫著濕冷的潮氣。那個清晨,打印機突然“咔咔”作響,像個哮喘病人般卡住了。老王費力地扯出被雨汽洇皺的稿紙,上面墨跡模糊,他湊近一看,不禁樂了——那句振奮人心的“踔厲奮發啟新程”,赫然被誤植成了“焯水發苦啟新程”。“噗嗤”一聲,老王笑出了眼淚,眼角的皺紋像盛開的菊花。他拿起桌上那支陪伴他多年的紅鋼筆,在故障代碼旁龍飛鳳舞地批注:“機器同志,火候不夠啊!這‘踔厲奮發’得是大火爆炒,香氣撲鼻,哪能‘焯水發苦’呢?”從此,老王的辦公桌便成了他與AI無聲較量的戰唱—左邊,是他從舊書市淘來的、泛黃的《人民鐵道》合訂本壘成的“碉堡”,里面記載著鐵路發展的崢嶸歲月和幾代鐵路人的熱血青春;右邊,是閃爍著復雜參數和數據流的AI終端,如同深不可測的“戰壕”。而辦公桌中央那盆老王精心侍弄的文竹,卻仿佛一個狡黠的旁觀者,正用它新長出的、嫩綠的枝蔓,悄悄繞過鍵盤的邊緣,纏住了連接AI終端的數據線,像是要在無聲中扼住科技的“咽喉”。
如今,宣傳科的年輕人總能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老王那支磨得發亮的英雄牌鋼筆,與小巧玲瓏的U盤,并肩靜立在一個素雅的青花瓷筆筒里。那筆筒,還是他當年在苗嶺小站時,一位苗族老阿媽送的。鋼筆與U盤,一舊一新,一靜一動,像一株被精心嫁接的臘梅,左邊枝頭綻放著醇厚的墨香,右邊梢頭吐露著冷冽的數據之光,倒也生出一種別樣的和諧。老王依然在每個起霧的清晨或靈感迸發的午后,習慣性地在蒙著水汽的玻璃上寫字。粉筆留下的蒼勁有力的印記旁邊,總會適時地跟著AI用熒光綠字體彈出的修改建議,那些建議如同老柳樹枝干上萌發的新芽,在遒勁的舊枝旁怯生生地探頭,帶著一絲對傳統的敬畏。
一個秋雨淅瀝的加班深夜,當老王在AI生成的“構建智慧鐵路云平臺矩陣,賦能現代化綜合交通體系”這段略顯生硬的文字后,親手補上“就像當年苗嶺小站,我們手持連枷,在鐵道線上組成的那道無堅不摧的連枷陣”時,他深吸一口氣,按下了回車鍵。剎那間,仿佛有什么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回車鍵竟像一顆投入靜湖的石子,濺起了滿屏溫柔的月光。那光芒,清澈、皎潔,與四十年前他趴在苗嶺小站煤油燈下,在稿紙上寫下“苗嶺”二字時,窗外悄然灑落的那一縷清輝,在時光的兩端,跨越了技術的更迭與歲月的鴻溝,精準地對接、共鳴,完成了這首傳統與現代、人文與科技交織的《粉筆與藍光的對位法》的輝煌終章。辦公室里,藍光與月光交融,粉筆末的微塵在光柱中舞蹈,一切都和諧得恰到好處。
免責聲明:本網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本站觀點。所轉載內容之原創性、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