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烏蘭牧騎小分隊
2017年1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寫給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的一封回信中指出,60年來,一代代烏蘭牧騎隊員迎風雪、冒寒暑,長期在戈壁、草原上輾轉跋涉,以天為幕布,以地為舞臺,為廣大農牧民送去了歡樂和文明,傳遞了黨的聲音和關懷。筆者認為,這封回信不只是寫給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的,也是寫給內蒙古自治區烏蘭牧騎演出隊的,同時也是寫給我們全國鐵路專業和群眾文化工作者的。筆者作為一名年值八旬的烏蘭牧騎老隊員,憶及當年往事,不禁感慨不已,也無愧年華流失。
烏蘭牧騎,蒙古語原為“紅色的嫩芽”,后被引申為“紅色文藝輕騎兵”。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誕生于1957年,一共9人,不受場地、舞臺、布景等條件限制,隨時隨地可演,節目自行創編。1964年末,北京鐵路分局提出了“把文化生活送到偏僻沿線”的口號,號召文化宮、電影隊的群眾文化工作者走出劇場,深入沿線,開展“流動俱樂部”活動,到偏僻的鐵路沿線小站和工區去傳播文化種子。不久,北京鐵路分局組建了一個包括筆者在內的3人文化工作小隊,活躍在管內最偏僻的豐沙線上,被譽為“豐沙線上的烏蘭牧騎”。
當年,這條鐵路沿線共有12個中小車站和26個工區,文化生活極度貧乏。“豐沙線上的烏蘭牧騎”成立后,既教唱革命歌曲,也講革命故事;既代售各類圖書,也輔導文藝活動;既美化站區環境,也開展通訊報道,備受職工、家屬和站區附近農民的歡迎。豐沙線上有一個名叫五角樓的半道工區,由于地處偏僻,當我們3個人步行4公里、攜帶大小14件200多公斤的物品穿越一條900米的隧道到達這個工區時,工區內外像過節一樣,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當天晚上,筆者先為這里僅有的14名養路工和10名家屬教唱了一首歌曲《我們是光榮的養路工》,繼而又表演了評書《抗日名將吉鴻昌》,緊接著我們就在炕頭上架起了放映機,放映了電影《昆侖山上一棵草》。
時隔半個世紀,筆者對在烏蘭牧騎小分隊工作的那段時光,仍舊記憶猶新。在那里,我們為豐沙線職工、家屬和各個站區周邊的農民放映的電影名片多達百余部,如《白毛女》《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山間鈴響馬幫來》等,很受觀眾歡迎。當年,在搞好電影放映工作的同時,每到一個站區,筆者就利用白天的充裕時間深入采訪,并認真撰寫不同體裁的各類稿件,向鐵路內外報刊投稿,先后發表的通訊、詩歌、報告文學和通訊作品達136篇;在大力開展大唱革命歌曲活動中,筆者還教唱了不少革命歌曲。在每場電影放映之前,筆者都把歌詞投射到銀幕上,教唱當年最流行的電影插曲,不到兩個月的工夫,整個豐沙線,不論是站區還是偏僻農村,到處都可以聽到唱《學習雷鋒好榜樣》和《唱支山歌給黨聽》等歌曲的歌聲;與此同時,筆者還相繼創作、改編、發表并演出了不少評書作品,如《劉胡蘭》《董存瑞》《抗日名將吉鴻昌》《王杰舍身救民兵》《階級感情千斤重》等。這類評書小段兒在曲藝界通稱“萬字活”,每段兒1萬字左右,不長不短,場地不限,演員觀眾,交流不斷。講至精彩之處,必定掌聲連綿;大凡情景動人時,熱淚定灑席間。后來,根據觀眾要求,在放映電影之前,筆者除了教唱革命歌曲之外,還先為觀眾加演一段評書。在開講之前,我們先用幻燈片將評書小段兒的名字打在銀幕上,然后再用麥克風當場表演,觀眾頻報掌聲。
后來,筆者還就地取材,先后根據舊莊窩養路工區和邢家堡站站長趙昆的先進事跡,創作了相聲《表揚誰》和三句半《老解決——趙昆》,不僅輔導業余演員進行了現場演出,而且兩個段子還刊登在《京鐵工人》報上,令豐沙線上的職工和家屬備感親切。
1965年,我們這支“豐沙線上的烏蘭牧騎”演出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同年8月6日,《人民鐵道》報發表了筆者的文章《活躍在豐沙線上的“烏蘭牧騎”》,報道了烏蘭牧騎小分隊在豐沙線上的戰斗與生活;9月19日,《京鐵工人》報也發表了約我撰寫的文章《把革命文藝送到沿線去》,編輯李連生同志還加發了一篇文藝短評。與此同時,《北京晚報》也介紹了“豐沙線烏蘭牧騎”小分隊:“3個月來,跋山涉水,走遍了豐沙線上的每個小站和工區,做到了既是放映隊,又是宣傳隊和文化工作隊,受到了群眾的歡迎。”
作為鐵路系統烏蘭牧騎的一名老隊員,筆者認為,若想抓好文化建設,各級領導不僅要有陣地意識,而且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應該關注那些在最艱苦、最偏僻的鐵路沿線工作的鐵路職工,因為他們最需要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筆者深信,我們鐵路系統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能用腳步丈量一條條偏僻的鐵路線路,像草原上的烏蘭牧騎演出隊那樣,扎根基層,服務基層,與鐵路沿線的廣大職工和家屬手牽手,心連心,扎根鐵路,情系群眾。烏蘭牧騎長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藝術,藝術需要人民。
免責聲明:本網站所刊載信息,不代表本站觀點。所轉載內容之原創性、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自行核實。
鐵路資訊
- 農歷小年車票開售 鐵路春運售票超1億張08:09
- 這一年,你的平安有鐵路人在守護08:09
- 京張“四電”通過初驗08:08
- 鐵路新裝備拉動“公轉鐵”08:07
- 推進安全生產整治有新招0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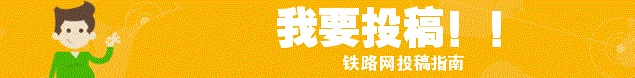





網友評論僅供其表達個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立場。